

公元446年兴泊证券,北魏太武帝突然下令焚寺诛僧、熔像收田,开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运动。过去,学者多将原因归于兵变频发、沙门秽乱或纯粹的佛道争宠斗争。
如果细致研究时代背景,就不难发现事变幕后的汉化转型。拓跋焘的灭佛举措,不过是压制旧鲜卑贵族,维护自己的皇权集中。虽没有把事情彻底做绝,却为后来的完全转向订立基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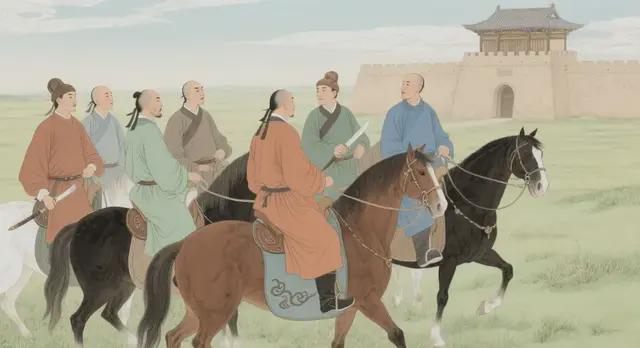
定都平城后北魏已开始逐步走向汉化
早在398年,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,就决定把佛教当作收揽人心与文化转型的双重工具。此前,北方的庙宇数量非常有限,本身也被视为某种西域外道,所以长期停留在不温不火状态。反倒是南方地区,受海上来的天竺、扶南使团影响,在普及推广方面略胜一筹。考虑到佛寺背后的金融、物流属性,这些差异必然是经济收益差距。

早期北魏还只是北方群雄之一
随着永嘉之乱爆发,以及稍后的南北对立格局稳定,北方的佛寺数量开始明显上升。其中缘由之一,便是具备保境安民职能,可以为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提供庇护。同时,强调超脱的哲学倾向,又对生活在高压环境中的人心有安慰效果。即便家缠万贯、拥兵自重的富户,都需要用其思想进行排解。至于立足未稳的蛮族君王,更需要借用其庙宇网络,达到快速敛财、协助恢复秩序和赋予神圣合法性等目的。

平城时代北魏的皇宫隔壁就是寺庙
因此,道武帝拓跋珪对佛教表现出极大虔诚,颁布诏书肯定其思想“济益之功,冥及存没”。甚至允许寺庙与自己的宫殿并排建造,还通过法律手段,给予僧众们单独身份和免税田产,连没有皈依的普通佃客都享有免征权益。彼时,佛教系统地位飙升,几乎可与代表世俗权力的鲜卑皇权并列。

北魏与刘宋的南北对峙
这番看似委屈自己的做法,果然让北魏国力稳步增涨。仅仅到太武帝拓跋焘继位,已是华北各势力中最具潜力的政权。除击败辽东和蒙古草原的同族远亲,还多次对匈奴人的胡夏呈碾压之势。即便遭遇南方刘宋帝国干涉,仍旧在多线作战中获得完胜。帝国版图也从平城附近,稳步拓展至洛阳、长安等中心区域。

鲜卑军功贵族与汉人士大夫之间素有冲突
此时,武力征服的比重渐渐下降,推广合理文治的紧迫性日益抬升。于是,以崔浩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开始成批进入庙堂。另有寇谦之等道士,凭借汉人宗教领袖身份入阁,逐步掌握大政方针的话语权。在后来的灭佛运动中,两位舆论领袖都发挥着关键作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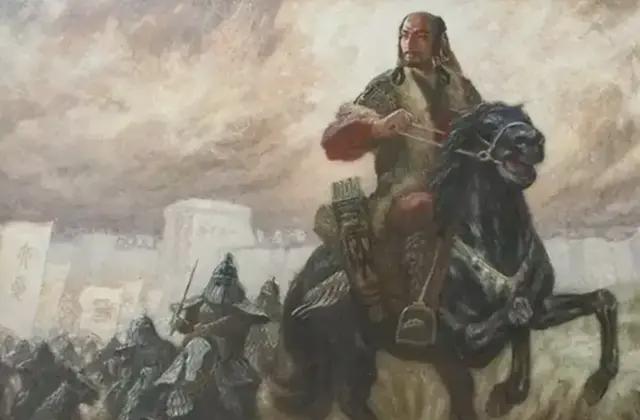
在执政前期拓跋焘依然遵循先前的崇佛路线
不过,真正能拍板执行灭佛政策的还是拓跋焘本人。随着帝国疆域开拓至黄河南北,治下汉人数量已完全超过鲜卑各部。若不能将他们迅速归为编户齐民,就会沦为地方贵胄的私人附庸,进而危急皇权本身。佛寺系统只是在表面上看似游离于世俗之外兴泊证券,实则多与贵族们形成攻守同盟。要么借用对方名义发展,又或是联手经营促进共同富裕。

士大夫与道士合流开始抢夺至高地位
关键时刻,司徒崔浩、道士寇谦之提出激进的“周孔方案”。其内容大致如下:
1 以礼代佛--用郊祀、宗庙、明堂等儒家礼制重新叙述皇权,彻底摆脱“胡族巫—佛杂糅”的旧式合法性;
2 编户代寺--将寺院荫附人口重新纳入州郡户籍,直接扩大税基与兵源;
3 华夏正统压制部落贵族--借儒家“天命—德运”话语削弱鲜卑旧酋对皇权的制衡。
此外,崔浩还献上自己编纂的《国记》,直接将拓跋氏的起源追溯为轩辕苗裔。寇谦之则借“老君授符”神话,为其套上太平真君头衔。两者共同构成一条充满排他性的彻底汉化路线,准备对只是过渡品的佛教大开杀戒。换言之,灭佛举措只是工具手段,帮皇帝汉化集权才是根本目标。

崔浩的正统论证 非常符合拓跋焘需求
公元444年,拓跋焘迫不及待的颁布诏令,严禁王公或庶人私养沙门,尝试斩断寺庙与地方世俗力量的联系。
两年后,太武帝西征关中镇压卢水胡叛乱,却被长安当地的寺庙气到爆炸。不但发现私藏兵器,还查出酿酒、敛财等辣眼睛行为,甚至有僧侣与女子私通。故而下令彻底禁佛,宣称要诛杀敢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、铜人者。即便留在平城的太子拓跋晃也接到类似指令,要求他将运动推广至全国各地。

太武帝一声令下开始对各地寺庙进行剪除
然而,佛教在北魏深植部曲经济。各地寺院占田动辄千顷,依附人口约有50万众,几乎能与世俗屯田系统分庭抗礼。若骤然废除,势必引发经济震荡,催生大批流民暴走叛乱。许多鲜卑旧贵或汉人豪强,也早已和寺院结成利益共同体,不会甘心在危局中束手待毙。尤其前者,非常担心自己因汉化集权而失去特权利益,形成动摇时局的最强反作用力。

作为经济支柱遍布各地的寺院显然很难被迅速取代
于是,太武帝采取选择性加速。虽然坚持用暴力剪除寺庙体系,却绝口不提“周孔圣教”,给未来回转留下余地。在初步稳定鲜卑贵族的情绪后,又跑去洛阳置办太学、祭祀孔子,试图用儒学教育吸收原属寺院的识字阶层。乃至将强行还俗的僧众编入史馆,继续承担抄写、校勘等工作,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文官班底。

鲜卑贵族为首的地方派多对灭佛运动阳奉阴违
他的儿子拓跋晃更是阳奉阴违。虽下令焚毁浮屠、伽蓝,却有意放缓执行时间,并暗中保护一些僧人逃脱。甚至偷偷隐藏雕像与经文,为以后的政策翻转做好准备。其他鲜卑贵族也跟着模仿,庇护距洛阳不远的嵩山少林,让寺内僧人能连夜把经典藏于石壁。

嵩山少林就在这场劫难中获得保护
可惜,某些地方官吏为借机表功,自动开启比狠模式。例如青州太守就将佛像捣毁后熔铸为佛血钱,还针对性极强的印有“太平”字样,丝毫不顾及百姓是否愿意使用。邺城的3000僧尼则被收编进军队,不从者直接拉去漳水边活埋。至于起始点长安,更是出现用马匹活活拖死和尚的残酷场面。

邺城僧众们远没有少林同僚幸运
讽刺的是,这场充满帝王心术的灭佛运动,始终没能达到太武帝追求的理想效果。许多贵胄都偷偷收留僧众,连太子都私留数十僧于苑囿,直至自己郁郁而终。作为鼓吹者之一的崔浩,很快因国史之狱被诛。拓跋焘则饱受头风折磨,还因为胡乱服用寇谦之的丹药造成身体每况愈下,于452年被宦官宗爱弑杀在永安宫中。

拓跋焘最后在病痛中遭宦官宗爱弑杀
随着太武帝驾崩,持续六年的灭佛运动宣告破产。虽然华北的佛教势力陷于衰落,但更大紊乱却出现在北魏皇族内部。等到太孙拓跋濬继位,立即诏复佛法,算是将皇爷爷的努力付之东流。

风波过后北魏帝国依然选择庇护寺庙
当然,拓跋焘的剑锋并非真要斩向佛陀,而是针对鲜卑贵族的卸磨杀驴。在他死后三十多年,又有魏孝文帝靠迁都来强行汉化集权,却在六镇叛乱与河阴之变的血肉磨坊中走向失败......

(全文完)
鑫东财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